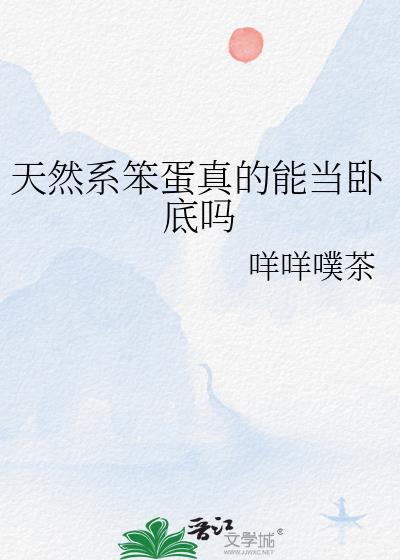时有幸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淑寒小说baixingdai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是装傻充愣。
他臭不要脸:“知道你们这里有句唱词是美满无他想,黑甜共一乡,我赶着回去感受了,给地道的苏州男人铺被窝。”
江知羽听完服了,两人拌着嘴回到奶奶家,付芬在擦书柜里的相框。
发现有江知羽出镜,戚述不急着休息,没了那股花里胡哨的劲,一本正经与付芬攀谈起来,企图以此多看几眼照片。
小知羽和长颈鹿合影,小知羽当上少先队长,还有小知羽在花坛前面转着圈……
戚述也看到了母子的合影,之前江知羽给他看过手机里的扫描版,如今塑封起来的更有岁月感。
“他的妈妈走得早,太难受了。”付芬扶了下老花镜,“有次绒绒生病不舒服,一直在喊妈妈,又说他怎么也梦不到人。”
尽管老人只提到孙子,但语气低落,想来自身也很伤心。
这应该是一家人的重创和转折,若非早年出现人身事故,江锦昆考虑到配偶工作、家庭生活,都不可能去海外发展。
想到江知羽努力学习法语融入环境,每天独自赶着校车上学,戚述说:“他变得很坚强,有照顾好自己。”
付芬的话语含着骄傲:“学校排名这种东西我不懂,但我听说他读书比他爸还好呢。”
另外一本相册收纳了陈年的纸张,从报纸上规整地剪了下来,均是孟佩彤当年执笔的新闻稿。
征得同意之后,戚述翻了几页,孟佩彤的行文很有活力和韧劲,这两点也能在江知羽身上看到。
他了解孟佩彤已不在人世,出于不想撕开江知羽的旧伤疤,没有询问过事故缘由。
“绒绒八岁的事情,他妈妈去火情现场,谁想得到会爆炸第二次。”付芬回忆,“所有人都烧伤了,救护车都拉不过来。”
那时候孟佩彤离爆炸点很近,当时医院就让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,在重症监护室里续了足足一个月。
不算丰厚的积蓄花光了就贷款,没日没夜地耗在医院走廊,这些根本算不上是最痛苦的事情。
孟佩彤烧伤得太严重,付芬光是看到就落下泪来,根本没勇气细瞧,难以设想伤者有多么痛苦。
她和江锦昆最开始不敢让江知羽去看,就硬着头皮瞒了一会儿,后来江锦昆认为江知羽有选择的权利,决定带小孩去医院。
江知羽当场就崩溃了,被仪器环绕的母亲没有意识,看不清本来面目,可血脉相连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?
赖在病房不肯走,被抱出来以后哭到晕厥,回家里依旧止不住发抖,吃不下东西又频频反胃,隔一会儿就要询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出院。
过了几天,孟佩彤短暂地恢复意识,江锦昆正好枯守在旁边。
付芬道:“后来我儿子就说不治了,照着她的意愿带她回家里。”
浑身插满管子,连翻身都做不到,并发症没有转圜余地,待在重症监护室不过是苟延残喘。
无论医学如何分析,家属在情感上无法割舍,祈祷能够多拖几天,盼望可以出现奇迹,但病人待在医院里,或许是感到折磨更多。
“回家熬了三天,大家都陪在床边。”付芬沉声说。
言语在此刻太苍白,戚述哑然地看着那些报纸段落,没多久,江知羽吹干头发从浴室出来。
见他们坐在客厅看相册,江知羽发现戚述的表情有些失神。
“人年纪大了,就是变得很啰嗦,和小戚讲了讲家里的事。”付芬率先说,“害得他心情跟着不好。”
江知羽隐约听到了些,不难猜出奶奶具体说了些什么。
实际上,付芬不怎么爱与外人提旧事,估计是瞧出戚述流露的黯然和疑惑,心知对方不会把这段过往当做谈资,所以忍不住与他感慨。
没让江知羽感到局促,戚述向付芬宽慰了几句,表示自己能被信任很惶恐,并没有为此烦闷。
他再问江知羽:“我这就改签班次,明天陪你去看看伯母吧?”
江知羽本来的确有些别扭,担忧戚述的反应太沉重和窘迫,这会让自己无言以对。
当下,他逐渐放松下来:“早十多年被我爸迁去巴黎了,在这儿扫墓也没地方。”
之后戚述去洗漱,来到江知羽的卧室,中间那张床足足有两米多宽。
床头看着有些旧,应该是从平屋搬过来的家具。
尽管保姆说过一嘴,戚述还是惊讶:“为什么你小时候的床会那么大?”
“一边我自己睡,一边放我的玩具。”江知羽解释,“曾有玩偶一米八高。”
床单都散发着阳光的气息,保姆都已经打点好了,他俩各盖各的棉花被。
戚述靠左,江知羽靠右,中间宽敞得能再睡两个。
虽然两人亲昵过许多次,但今晚躺在一处,莫名有着复杂滋味。
江知羽裹住自己,故意克制着动作假装安稳,连自己的翻身次数都限制,却直挺挺地睡不着。
他想象戚述过来占便宜,有些生闷



![[综英美]蝙蝠家唯一指定普通人](http://baixingdai.net/images/121/2e4c61a6c35697b2be682653f51da03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