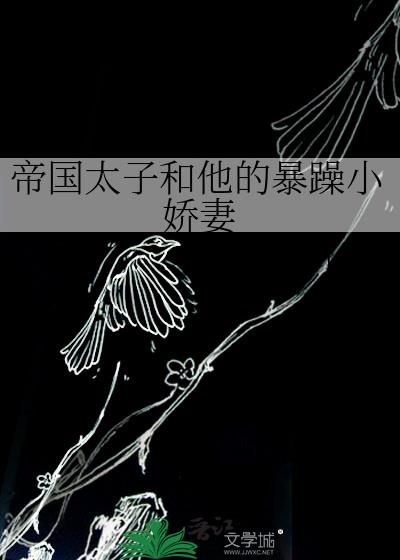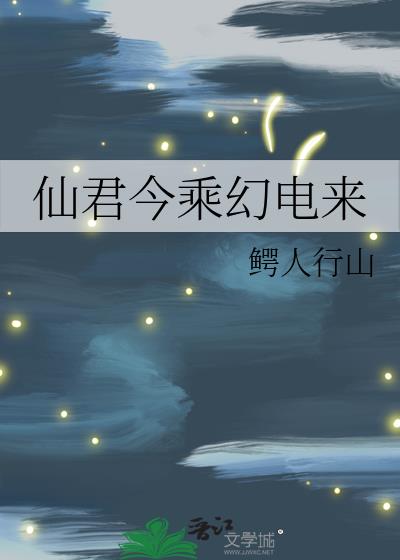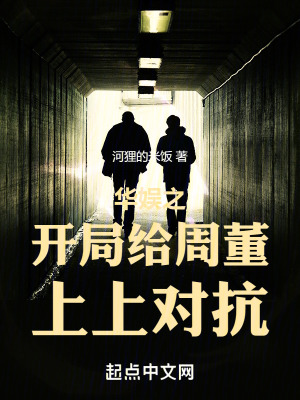持一念以成魔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淑寒小说baixingdai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满仓给李明海说了师傅留下的地址,李明海倒是认识,和满仓并肩而行,感慨道:看不出来,你做事很沉稳。有些地方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,可以给我说说?
海哥见笑了,满仓道:有什么不明白,我也没有做什么。
于是李明海问出了心中的疑惑,比如他称称都很足了,还要给人家添一点?为什么还称还要给摊主五毛钱,明明是我们给他带来了生意,他应该感谢我们才是。
满仓给李明海递上一根烟,自己点了一根,说:因为人性
怎么讲?李明海,一边接烟,一边问道
人都皆有贪欲。
《山海经》里说:巴蛇吞象,三岁方吐其骨,被庄子浓缩为:人心不足,蛇吞象,虽是夸大的说法,却映照出人性深渊中永不停歇的欲望。市井巷陌的烟火气里,贪欲正在以最朴素的形态上演。穷人没有钱,便想有钱,富人有钱,想更有钱。男人没有女人的时候,看到谁都漂亮。当娶了媳妇,还是觉得别人的老婆漂亮,哪怕自己老婆本来就很漂亮。女人想自己男人富有,帅气,哪怕自己的男人本来也不错,还是觉得别人男人好。贪念如同苔藓,在生活的缝隙里悄然滋长,编织成看不见的欲望之网。
满仓看看不解的李明海,解释说:你给人称红薯干,是不是都想足斤足量?这是基本要求,再给他们添加一点,就是满足了他们的贪欲,再者,他们觉得给他们添一把,觉得我实诚,憨厚,也是满足他们贪欲之一。好人是好,但是好人总是被欺负的对象,为什么?因为好人的贪欲不强,或者说能控制自己的贪欲。
再说摊主大哥,我们在他摊位边卖薯干,是给他带来人气。买薯干的人,不会就买一样撒,假如他摊位上有符合顾客的货物,只要价格公道,肯定就选购了,从这一点上讲,他是要感谢我们。为什么我要给他钱,还给薯干给他,一个道理,满足了他的贪欲。摊主和我们非非故的,看我们顺眼,就是先满足他自己要求的前提下,还有意外惊喜。当你不能满足他的贪欲,或者说你对他没有任何用,不能为他带来利益,无论你这么优秀,如何讨,他绝对怎么看你都不回顺眼的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往,天下攘攘为利而来,都是一个道理。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,虽然在说对人或物不可要求太高,但是从人性方面来讲,也是一个道理。
李明海听得直摇头,满仓道:就是爱占小便宜。他们爱占小便宜,那我就满足他,不就行了??
你大爷!李明海骂道:就说爱占小便宜不是得了?绕得我头晕。不过听你那么讲,好像也是那么回事。
李明海,满仓正色道:海哥,你大我几岁,我叫一声哥,你我脾气相投,我也拿你当兄弟,你记住一句话,我们不当坏人,但是也绝对不做好人!!
李明海不解地道:为什么?
满仓狠狠地道:好人是好,但是好人总是被欺负的对象!
这时满仓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,他怕控制不住会把自己点燃,他想到了自己父母,看见路边衣着破烂的人群,这里都没有大奸大恶的人,都是善良的好人,但是为什么好人就应该受穷,为什么好人就命中注定会受苦挨饿?
为何善良总要与苦难共生?这个困惑,恰似人类文明长河中永恒的诘问。好人,这个看似明确的道德符号,发现其内核交织着光明与阴影、崇高与困境的辩证统一。
古希腊城邦的集市上,亚里士多德用“中道“理论诠释美德,认为真正的善行应当介于鲁莽与怯懦、吝啬与挥霍之间。这种哲学思辨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论辩中同样回响。墨子主张“兼爱“的普世性,杨朱学派却质疑无差别利他的现实可行性。当宋明理学将“存天理灭人欲“推向极致,王阳明却在龙场驿的深夜烛光下顿悟:至善本在人心,却需在事上磨砺。道德准则从未静止,它始终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与人性进行着动态对话。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《目连救母》变文,描绘了孝子穿越地狱的壮举。这个佛经故事在民间演绎中,逐渐叠加了目连为救母打破戒律的情节。这种叙事嬗变揭示着深刻的伦理悖论:绝对的道德准则在复杂现实中往往陷入两难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,试图用恶行实现善果,最终在自我撕裂中完成救赎。善的纯粹性与其现实有效性,构成了永恒的张力。
好人注定受苦的宿命论,实则是特定生产关系的镜像投射。在《白毛女》的叙事框架里,杨白劳的善良成为地主阶级剥削的道德掩护。但若将视野投向江南市镇,晚明东林党人顾宪成在《朱子节要》中强调:士人当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“。这种将个体道德自觉融入社会改造的尝试,打破了善恶与阶级的简单对应关系。正如黑格尔所说:“悲剧的本质是伦理力量的冲突“,好人的困境往往折射着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。
鲁迅在《野草》中写下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“。这种对本质主义的双重消解,恰可作为剖析“好人“命题的棱镜——当我们试图用道德显微镜观察人性,看到的永远是测不准的叠

![[红楼]贾璋传](http://baixingdai.net/images/1436/b249882f968b0d4d65bb5a75f2031759.jpg)